
王计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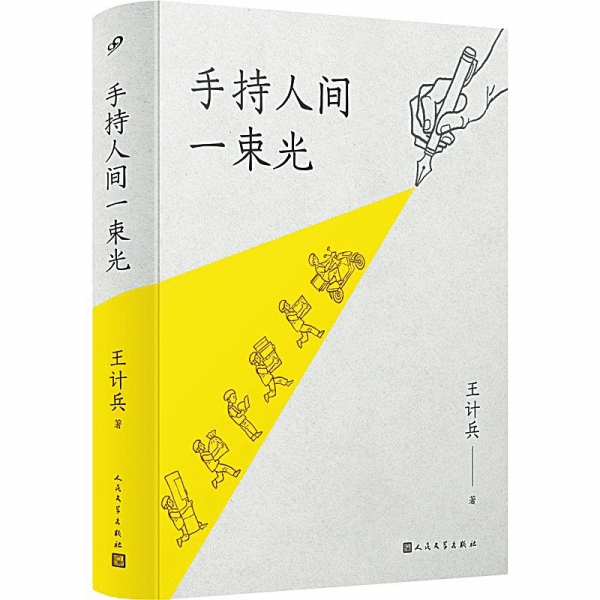
《手持人间一束光》书影。
华声在线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
“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赶时间的人/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
2022年,一首以送外卖工作为主题的诗歌《赶时间的人》在互联网上走红。随后,作者王计兵走入大众视野。他是江苏昆山的外卖员、一家小日杂店的店主,也是一名诗人。
今年上完“春晚”之后,王计兵没有时间跑外卖,但还是“赶时间的人”。他的时间被出版社安排的一场场宣传活动填满,在不同的城市间辗转。3月23日,王计兵带着他的第四本诗集来到长沙图书馆,与著名作家王跃文对谈。
“今年初才出版,这已经是第三次印刷了。”翻开《手持人间一束光》的封面,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本书责编郭良忠笑道。王计兵接过来,掏出随身携带的签字笔,飞快地为读者签名。
图书馆的落地窗外,春花正迎着和暖的风儿盈盈开放。他还签下了一句话——“人生就是在酿一场蜜”。
普通爱好
1988年,辽宁沈阳街头,一个来自江苏邳县的19岁建筑小工有了自己的爱好。
那正是“文学热”的年代,各类文学报刊很多,城市的旧书摊上总聚集着很多人。初二就因家贫辍学的建筑小工王计兵站在旧书摊上一本本地看五花八门的期刊杂志和武侠、言情小说。书乱,常有找得到上本找不到下本的情况,他按捺不住好奇心,于是学着理清故事脉络,在自己的想象中续写结局。
15岁就离开家乡四处漂泊打工,外面的世界和他在童年、少年时的想象大不相同。辛苦、劳累、孤独,循环往复,望不到尽头。“刚成年时,我猛然发觉人生没有什么出路。现实和理想差异非常大,很苦闷。”56岁的王计兵回忆,“我要找一种方式让自己变得踏实一些。我选择了阅读,越阅读,越感觉到文字的诱惑——书里总有些描写和我的心灵是贯通的。可能那个时代的诱惑也比较少,如果是现在我可能就喜欢刷短视频了”。
文字里的世界,成了独立于现实生活的“另一个世界”。他隐隐有了靠文字闯出一条生路的梦想。
他开始写微型小说。1992年,他的小小说《小车进村》在一家杂志上发表,后续又有多篇小小说刊登,他还收到过一位作家勉励他的信件。
但这没法支撑他成为专业作家。他写得昏天黑地,手稿却被父亲付之一炬。人要活得现实一点,他还是去打工。新疆、山东、江苏昆山,当力工、小摊贩、拾荒、开日杂店,结婚、生子。
生活总是受穷,这点让王计兵感到挫败。但他还是觉得,有个爱好,总比没有好。
20多年的时间,王计兵写作不留底稿,写完就扔。“丢掉幻想”,他发现自己喜欢写作这件事本身。“写作和别的爱好没什么不同。有的工友喜欢钓鱼,有的喜欢弄个乐器。当你爱上一件事情,时间越久就越舍不得放下。它改变我对生命的体验,让我过得有劲、有滋有味,改变我对生命的态度。”但从现实层面,爱好写作是“无用”的。家人不支持,他就藏着掖着写,不耽误“找生活”。他说,从来坚信写作于他而言是“无用之大用”,“写作有可能是我一个人的事,和别人无关”。
他没有办法拥有什么书,收废品来的旧报纸旧书就是阅读素材。也不太有写作空间,所以用圆珠笔,写在旧包装、烟盒、报纸上。后来,他学会上网,尝试着和论坛网友交流写作。有人建议他把文章改一改,改成形式短小、灵巧的诗歌。2009年,王计兵学着写诗。
湖南省会同县粟裕希望小学语文教师李柏霖长期带领孩子写诗歌,创建了“田野诗班”。李柏霖对我说,她早就读过王计兵和矿工王喜年、西北农民“田鼠大婶”裴爱民等素人作者的诗歌及相关报道,这对于她是莫大的鼓舞。她所在的小学,留守儿童占比超过一半,“这些孩子们在整个学业竞争和筛选体系里是不占优势,很多可能不一定有机会去上高中”。她感到心疼的同时,也在不断思考写诗这件事究竟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以及“什么是好的语文教育”。正是在王计兵这样的作者身上,她看到了一种可能:哪怕生活不那么光鲜,但贴近诗歌的他们,将来或许可以拥有一项爱好,一个出口。在生活的困难里拥有发现美的眼光和言说、表达的能力,去帮助自己幸福一点。
是大叔,也是“小哥”
“送外卖,算是我从事的最轻松的一种工作了。”他脸膛黑黑的,深深的笑纹绽在眼角。他曾在故乡的沂河里捞沙,被水中流沙不断打磨皮肤,火辣辣地疼。蹬车卖水果,江南地区多拱桥,他蹬着三轮车装着400斤的货物,每爬一个漫长的坡,就感觉到“心脏要跳出来”,两腿发软。
2018年,在自家日杂店守摊时,来了一个装电瓶车的人,他的主要客户就是外卖骑手。当时,王计兵一家已在昆山买了房,还贷款压力很大。他向这个人请教,自己能不能送外卖。对方说:“谁都能。”王计兵决定试试。刚开始,王计兵不会用外卖软件,找不到地图导航。第一单,他靠一路打听才找到了点餐人,超时了。
后来渐渐熟练。但这个年龄在同行里算老了,腿脚不如年轻人灵活。“我一天最多能送68单,平时是30多单。”而“单王”,能跑120单。但王计兵性格好,总是笑着,“五星”评价多。好的时候,能到手五六千元的工资,他觉得还不错。
王计兵喜欢雨天的单、长途的单,因为补贴高。长期的写作练习,让他在送外卖时蔓发了一种浪漫——骑车时,他总感到城市中有一些缝隙,吸引他去观察。砖隙的苔藓、金属上的锈皮,都收入他的眼睛,加冕诗性光辉。成为外卖小哥,也意味着不停在街巷中穿行,与不同的人打交道。王计兵自认是个沉默的人,但这样的交道,他很喜欢。
平台的算法催他争分夺秒,他开始习惯用手机语音记录这些观察和感悟,有空再整理为诗歌。“我的写作的风格和观察世界的角度发生了变化,我自己明显能感觉到。”
他采访身边的骑手们。写困在平台算法里的骑手的无奈,“骑手是一枚枚尖锐的钉子/只有挺直了腰杆/才能钉住生活的拐角。”写外卖员这一庞大的群体,“如果我来重写江湖/外卖肯定是江湖最大的帮派”。
他见过蜗居于烂尾楼里,靠手机和外卖颓然度日的年轻人;敬佩摔断了八根肋骨,出院后依然坚持送外卖,还跑成了“单王”的小哥。他遇到过刁蛮的顾客,也收到过宽容的安慰。于是在文字中阐明哲理,写下了他关于尊严与生活的沉思“请原谅这些善于道歉的人吧……生活之重从不重于生命本身”。
在长沙图书馆,王跃文翻开新书,朗读了一首让他印象深刻的作品《母亲的身高》:“身份证上没有记载/户口本上也没有记载/我只记得小时候/母亲背着我赶路/我曾伸手薅下/路边的狗尾巴草/只记得/割麦子的母亲低于麦草/拉车的母亲接近路面/母亲也到学校找过我/从初二教室的窗口/露出一颗头颅和半个肩膀/十五岁时我离开家/后来母亲中风,瘸了/再也没有站直过/回忆这一生,我居然不知道/我的母亲究竟有多高”。“我被深深打动了。”王跃文说。
文字照亮的微观生命史
19世纪末,诗歌已经日益把关注的眼光投向时代巨变下人们的处境、情感,以及对人类文明流向的关切。汉语现代诗诞生很晚,但也遵循着这一趋势。
王计兵自述,自己的诗歌是“被生活一口一口喂大的”。限于受教育程度,他看不懂很多著名的诗歌作品,承认远达不到那些诗人的底蕴和高度,他接受那些批评,但“写作依旧是我最喜欢的事情,我会写下去”。王计兵因“外卖诗人”的标签走红,他不讨厌这个标签。“我知道这种光芒带给我的帮助有多大。但我最怕的就是失去诗意。媒体终有一天会从我的身边离开,我回归平静之后,希望网友偶尔想起来再回头来看一下王计兵(的作品)。”
如今,素人逐渐从原指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对文学充满爱好的普通人,变成专指基层劳动者。在学界、新媒体平台、出版机构等力量的合力推动下,这些隐没于主流文学视野之外的素人写作者们,涌现了出来。
2014年起,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为基层劳动者组成的“皮村文学小组”授课。他称素人写作者为“新工人作家”。“新工人”即随着改革开放而产生的农民工群体,身上纽结着城乡双方的繁复矛盾和困境。他将他们的创作放置在20世纪中国形成的人民文艺的传统中考察,认为这些渗透着劳动者尊严感和包容态度的文学表达是一种社会实践,是新时代人民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曾在“素人写作和新大众文艺”座谈会上表示,在高度流动的、复杂的社会中,素人写作有助于打破人们仅以职业身份发生关系的局限,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打开、交流,穿越社会身份的藩篱,实现相互认识和联结。建议素人写作要“见素抱朴”,把独特的经验、感受作为自己的根本。
“这波宣传期过去,我还是要继续送外卖的。”尽管现在已经不再有太大的经济压力,王计兵还是不打算离开外卖行业。只是心境有所不同,如今更类似于一种采风和生活状态的调节——他还想将笔伸向更多的题材和体裁。他坦言,那些看向自己的目光不一定都是对他诗歌的欣赏,也有悲悯和猎奇。但他并不感到难受,只是督促自己要努力。
素人写作,是“劳者歌其事”。今天,《诗经》仍能带我们回到两千多年前的劳动现场:“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春日迟迟,采蘩祁祁”……我读到一位网友的评价:也许未来,一些基层劳动也成为过去的记忆,这些劳动者的诗歌或许能抛开掺杂其中的猎奇目光,在更长久的时光里以质朴的文字力量依旧获得一次次共鸣。
责编:欧小雷
一审:欧小雷
二审:蒋俊
三审:谭登
来源:华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