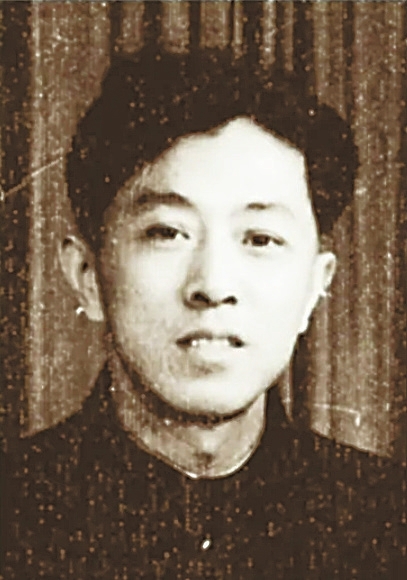
彭燕郊(1969年摄于长沙)。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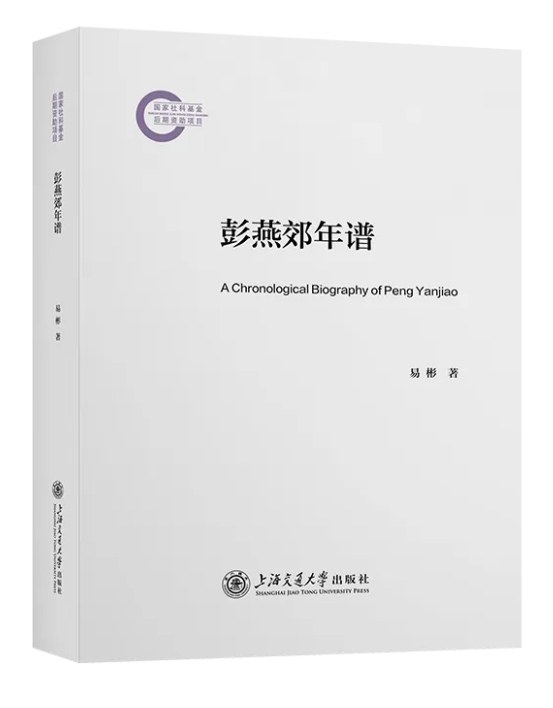
《彭燕郊年谱》。易彬 著
易彬
一
彭燕郊原名陈德矩,1920年生于福建莆田,1938年加入新四军,此后,在桂林、重庆、香港等地从事创作和文艺活动。1949年,在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后曾短期在《光明日报》工作。1950年后定居湖南,先后在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1955年因“胡风案”牵连入狱,后在街道工厂劳动20余年。1979年起,到湘潭大学中文系任教,1987年退休,有四卷本《彭燕郊诗文集》以及大量散佚的作品。
彭燕郊被人们所认知,首先因为他是一位诗人。1939年,《冬日》等诗四首以《战斗的江南季节(诗集)》为题,刊载于重庆《七月》的头条;至新中国成立时,已出版《春天——大地的诱惑》《第一次爱》等四种诗集,已有诗名。新时期以来,彭燕郊进入新的创作期,迸发出了强大的创造力,写下了《小泽征尔》《混沌初开》等名篇。在现当代诗歌史上,彭燕郊是极少数始终葆有诗艺探索激情的诗人,其晚年写作,特别是“衰年变法”的形象可谓是孑然独立于当代诗坛。
与此同时,彭燕郊也是一位重要的文艺活动家、民间文艺工作者、诗歌教育家。梅志曾称彭燕郊为“文艺组织者”,晚年的他花费大量心力策划或主编多种外国文学译介丛书(刊),如“诗苑译林”“现代散文诗译丛”以及《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等;在民间文艺工作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曾与钟敬文合编《光明日报》的“民间文艺”副刊,在大学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出版《湖南歌谣选》,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南分会副主席,主持民间文学刊物《楚风》等。而他在大学课堂的“诗歌研究”授课内容也曾结集为《彭燕郊谈中外诗歌》出版,彭燕郊先生的创作以及他所从事的文艺活动、民间文艺等方面的工作,在文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因为三十岁之际——1950年来到长沙后即定居于此,出生于福建的彭燕郊早已被看作湖南诗人。而且,湖南文学界多视彭燕郊为大师级的人物。这种偏爱很容易理解。一些外省的评论者如吴思敬、韩作荣、王光明、陈太胜等,也给予了彭燕郊非常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位似被忽略、却对诗有着深入、精到理解、卓尔不群的真正的诗人,却没有得到重视和应有的评价”“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诗人”,彭燕郊“早期诗作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可被列入新诗史上最好的作品之列”,也是“中国现代继鲁迅之后在散文诗这一文类的写作上作出最重要贡献的作家”。尽管从目前来看,彭燕郊尚未获得广泛的诗名和重要的文学史地位,但这些关于形象、精神与写作的声音显示了彭燕郊评价可能达到的高度,意味着更大的研究空间还有待打开。
二
说起来,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2005年4月,借着一次诗歌活动的机会,我与诗人彭燕郊先生商定做系列访谈的事宜,8月初,访谈正式开始。此前,虽在一些场合与燕郊先生有过照面及短暂的交谈,也和几位诗友去过其家中,但真正的交往无疑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此后两三年内,去彭家不下数十次,多半是做访谈或是核实访谈文稿。偶尔也会去闲聊,或者友人来了,去讨几张省博物馆的赠票。
如今,《彭燕郊年谱》终得出版。书有几十万字,看起来确实有一点厚,但只要把它平摊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厚度也就不那么醒目了吧。
不同于别的著述文体,年谱是关于时间的书。程光炜老师为年谱所写序言中,有一段令我的内心有特别的触动:
“我是有一个疑惑,像易彬这个年龄的学者,为什么会花上大把时间、投入如此多的精力,愿意与老一代诗人的苦难史同行呢?上次是自由主义诗人穆旦,这回是左翼诗人彭燕郊。一个能找到的理由就是:他是一个愿意沉浸在历史悲欢之中的学者,也可以说,是一个为这段行将消失的历史进行冷静的整理性研究的学者。”
彭燕郊的重要性,我是愿意相信的。而作为一名朝向“历史”的研究者,我乐意以一种“冷静”的方式去处理,同时,以尽可能宏阔的眼光去发掘与打量,力图找到那些通向历史的道路,揭橥历史对象身上那些未被注目但独特的、充盈的意义,而不在乎其重要与否;而如何安顿“历史悲欢”,又如何为自己的持续工作找到更可靠的认知视角与情感基点,在此前的工作中自然是有所考量的,在未来的研究路途之中,还将继续摸索和体察。
我愿意再重温由访谈而走进燕郊先生的生活的时光,为此,还特意翻出那篇《“单纯就好!”——纪念诗人彭燕郊先生》,一看到开头就徒生感慨:“桌上放着厚厚一叠打印的谈话稿,它不过是2005年夏天以来诗人彭燕郊先生与我的谈话中化为文字的那一部分,更多的,更生动的,已化入无边的黑暗之中”——不仅仅是当时有很多未能化为文字的内容,日后的记忆也有盲区:2019年去广州看望燕郊先生的夫人张兰馨老师的时候,因其正在整理燕郊先生的日记而有机会看到跟自己有关的内容,其中2008年2月12日(正月初五)有记:“下午五时半韦白来,承约去雅景隆苑晚餐,同席者旭东、易彬、远人、易清华、路云及韦白的一位老友,承易彬赠巧克力一盒。”这是跟燕郊先生的最后一次会面,情形还历历在目,记得白米粥端上来之后,燕郊先生对小小的一碟配菜(橄榄菜)赞不绝口,走的时候还特意打了一小包带回家,但“赠巧克力一盒”之事却已全无印象了啊——也是当日席间,燕郊先生悄悄告诉龚旭东和韦白“身体不适,脖子上忽然长起一个大包”,但“不想让夫人和正在家的女儿知道”;饭后回家路上,两人查看了大肿块,当即建议“去医院检查”,这样的关乎生命的细节也是日后经龚旭东老师讲述才知晓的。个人记忆与视角尚且如此,由此转回到年谱工作,从时间的长河中博采各类文献,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不就是将一些“已化入无边的黑暗之中”的历史找回么?
在《一朵火焰》中,彭燕郊描摹的其实也是“诗的火焰”:“一朵火焰,有柔和的光/恬静的、越看越亲切的光/并不摇晃,并不闪烁/可以长久注视的光”。愿这本记载一位还不是特别知名的诗人、历十数年终得以完成的书也能获得“长久注视”,找到它自己的读者。也愿那些从历史长河中捡出的、纷繁芜杂的文献,能闪烁光芒,能得到回响。
责编:欧小雷
一审:欧小雷
二审:蒋俊
三审:谭登
来源:华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