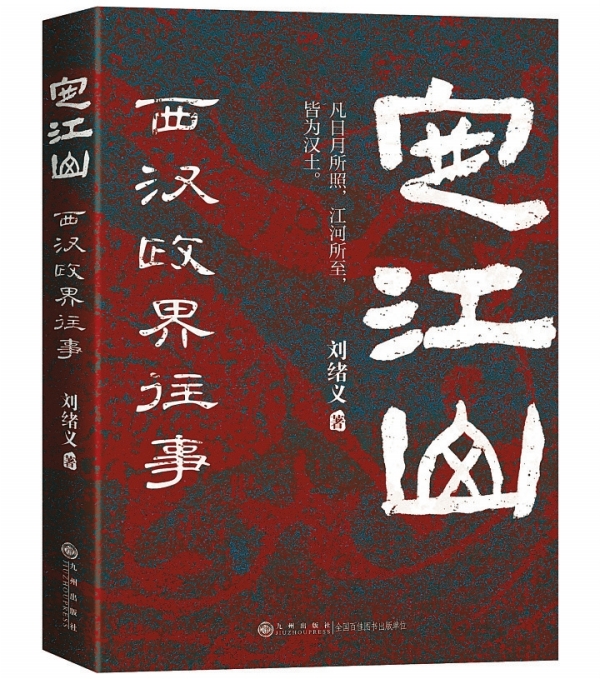
陆信礼
西汉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奠定大一统国家格局、塑造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关键时期,历来受到治史者的偏爱。知名学者刘绪义的新书《定江山:西汉政界往事》就是这一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该书从“大国之治”的视角出发研究西汉国家治理的得失,深入探索了西汉时期国家治理的经验与奥秘。
以小见大,聚焦制度和文化
该书并没有采取全史的视野,通览西汉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全方位历史,而是以关键问题为线索写作。作者力图以小见大、以小求大,重点聚焦制度和思想文化,分析论证它们在西汉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以简洁严谨、清新的笔法来表达观点思想。
作者突出了政治与学术这两条线索,吸收前贤的研究成果,吸纳出土文献资料,重新审视了传统的研究观点,提出了一些颇具创见的结论,为理解西汉国家治理的曲折变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有利于推动和深化国家治理的研究。与传统从黄河中上游的方向来审视西汉政治的不同,他在书中选择了南方的楚人和东海之滨的齐鲁这两类人作为观照的主体。
制度抉择,江山的定守之道
建立西汉的是楚人,奠定西汉政治制度与国家治理基础的是楚人,而绵延西汉两百多年的思想学术之争的却是齐鲁士人。影响或者左右西汉国家治理的恰恰也是这两类人。然而,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人民”,而是“江山”。也可以这么说,“定江山”的是楚人,“守江山”的依然是楚人,而齐鲁士人却始终介入并搅扰西汉江山的“定”与“守”,直到王莽代汉。前者代表“政治”,后者代表“学术”,整个西汉史就是这两大群体在政界和社会文化中的纵横捭阖。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制度选择的正确,是定江山的根本;思想意识的适配,是守江山的根本。”
西汉的江山是刘邦从秦朝打下来的,作者肯定了秦制的优点。事实上,西汉定鼎以后长时间承袭的是秦的法制,近年来出土文献也确信秦朝的法制并非残暴,因此作者指出,秦朝的统一时间太短,六国故地对秦的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接受和适应期,假如给秦始皇留出足够的时间,秦朝制度的成功是有可能的。
刘邦和项羽之间的斗争,传统的观点是人才起决定性作用。但该书提出,军事、为政皆在得人,这一传统的观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刘邦在楚汉战争中的成功,制度的选择才是根本。事实上,秦灭之后,项羽的实力是刘邦的数倍。刘邦项羽力量的对比变化,恰恰是在项羽分封诸侯,定都彭城,自封西楚霸王之后。原因就在于,项羽选择了过时的分封制,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被证明为战乱的重要根源;而刘邦看到了秦朝郡县制的好处,采取了接受秦制的姿态,以统一天下为目的。大家才会用脚投票,选择好的制度,这就是项羽众叛亲离的原因所在,也是西汉开国后得以迅速安定的原因所在。
治国难题,政治与学术相互影响
阅读该书过程中,常让我想起马克斯·韦伯的名著《学术与政治》。古代国家治理的一条主线始终是王权强弱变迁和官僚势力兴衰的对比较量,西汉也是如此。
如果说楚国人选择并确立了西汉的制度,那么,齐鲁士人则致力于争取学术地位。传统的观点认为,儒家思想经过西汉的改造和重构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其实不然,作者从儒生在秦朝的地位、今古文经学的发展演进、儒的命运与人在秦汉时的作为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儒学在西汉的真实面貌,确立了儒学一尊只是经学者的一厢情愿。面对齐人在政治舞台上的“吃香”,鲁地儒生以经学为旗为自己争地位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异化了孔子儒学,士之“弘毅”精神消失。鲁地儒生不甘齐人靠骗术登堂入室,而致力于寻求为儒生谋地位,汉儒的学术就给人一种赌博之感。西汉自始没有出现韦伯所说的那种“我只为我的志业而活”的学者,只有以经学为自己谋地位的儒生以及率以“经术润饰吏事”的循吏。
一般地说,政治对学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西汉,学术对政治的影响更明显。该书揭示出一个现实,利益的诱惑导致学术思想偏离其独立的轨道,成为儒生集团谋官谋地位的武器和道具。儒学没有独尊,经学的解释权却定于一尊,最终帝王成了经学的最终裁判者。朝堂之上,盛世的祥瑞,末世的灾异,堂而皇之成为权力斗争的利器,至西汉末世,将灾难解读为祥瑞,最终断送了西汉的江山。这是贯穿西汉“大国之治”的难题,也正是该书发人深省之处。
读《定江山:西汉政界往事》时,轻松之中常给人以一种沉重感。这种沉重感又启迪人们进一步深思国家治理的奥秘。
责编:刘畅畅
一审:印奕帆
二审:蒋俊
三审:谭登
来源:华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