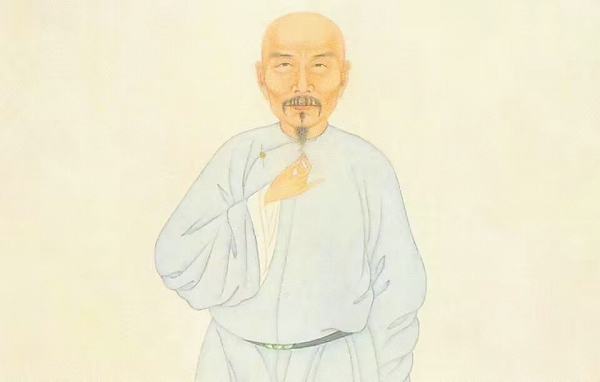
魏源像。(资料图片)
徐峰
近代湖湘人物群体多为高官,而魏源没当过高官,除短暂当过地方主官外,长期充当幕僚角色。
长期的幕僚工作,别人只是为长官代笔作文,他却是工作上与长官共同研究时代课题,工作之余深入开展学术研究,偶有闲情则“诗酒趁年华”,最终成为著名思想家、学者、诗人。
从学术思想来看,魏源经历了理学家、汉学家(今文经学家)、经世派实干家的持续转变,而见证这一转变的,是他的三本书。
《默觚》,是由读书笔记编辑而成的一本篇幅不大、内容全面的著作。全书分《学》《治》上下两篇,《学篇》十四、《治篇》十六,共一百六十五条,短则数十字,长不过七百余字。
这本小书在梳理中国传统学术流派时,指出汉学烦琐“饾饤”,宋学“心性迂谈”,提倡通经致用。更重要的是,《默觚》集中体现了魏源的哲学、政治、人才等思想。比如,魏源认为矛盾普遍存在且有主次之分,既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还要用辩证的观点看待事物的转变,因此,魏源总结强调“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这是其主张改革的理论依据。在认识论上,魏源持“行先知后”观,认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强调通过亲身实践才能认识事物。在政治上,他主张因时而变,反对泥古守旧,认为“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在人才观上,他的人才标准是“敏、周、暇”。“敏”就是眼光敏锐、当机立断,“周”就是思虑万全、洞悉底蕴,“暇”就是沉着从容;他还主张知人要知长短,然后“用人者,取人之长,避人之短;教人者,成人之长,去人之短”。
《皇朝经世文编》,是一本风行海内转变学风的书,也是魏源转变为经世派的代表作。
魏源能够编成此书,很大原因是身在陶澍、贺长龄的幕府,而二位都是提倡经世致用学风的封疆大吏。在他们看来,无论汉学,还是宋学,都是不问现实、不谈时事,无补于世道人心和国计民生。贺长龄有意将清代以来经世致用方面的文章汇编成书,在其幕府的魏源,就成为这一想法落地的不二人选。
魏源没有辜负这份信任。首先,他明确了必须遵循的“审取、广存、条理、编校、刊刻”五项原则,其中关键是“审取”和“广存”。关于选文章的标准,魏源认为“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凡适合于古代而不适合于今天、泛泛而论不切实际者,凡在前朝有用而今天没用的,都不选。
魏源从清朝初期到道光五年的时间范围里,从各家奏议、文集、方志等文献中,选取了二千二百三十六篇文章,涉及作者七百零二人。可以想象,编成这部书需要多大的阅读量!
两千多篇文章,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等八个门类,每个门类下再分若干子目。
《海国图志》,是以林则徐主持翻译的《四洲志》为基础扩编而成的,但已经远远超出了原书。
首先是编书时间之长。从1841年受林则徐之托起,1842年底完成《海国图志》五十卷,形成第一个版本。1847年,魏源将多年收集的资料进行增补,修订完成了六十卷本。1852年,他又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修订,篇幅增至一百卷。
其次是征引范围之广。按魏源的说法,《海国图志》是“以西洋人谈西洋”,完全有别于之前以中国人谈西洋的书。为何要如此呢?他说,“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要达到这一目的,就是广泛征引各种资料、各类著作,尤其是西人著作。
第三,是编辑体例之新。按道理,这应该是一部志书,实际却并非如此。这部书以中国传统的典志体为主,同时采用论、图、表配合的编撰方法,是一部综合性著作。就内容来看,按现在的学科分类,这是一部集世界地理、历史、风俗、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为一体的百科全书。
《默觚》是应时之作,《皇朝经世文编》是引领时代之作,而《海国图志》是划时代巨著。三本书,同一人,不同的是思想。
责编:刘茜
来源:华声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