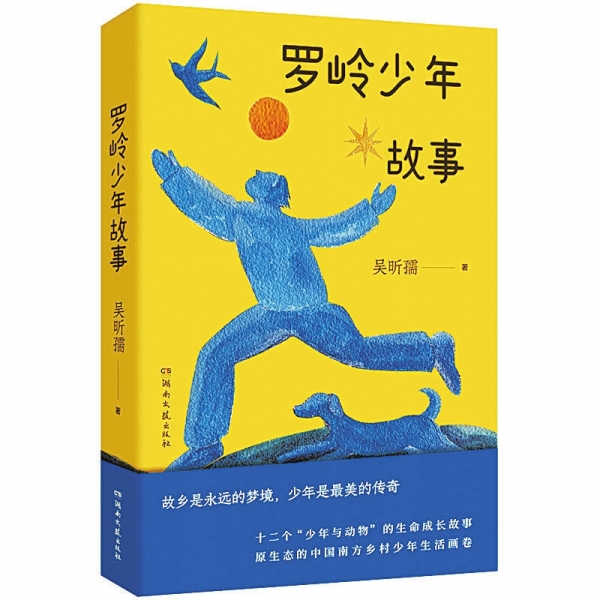
张家鸿
品读短篇小说集《罗岭少年故事》(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5年8月),如同走进作者吴昕孺的少年时光。虚构与想象交织其中,罗岭少年身上发生过的故事,读来趣味横生,引人入胜。
首先,它的情节富有谐趣,这也成为文本充满感染力的重要来源。《雀殇》中,匹超夸口说他能用眼力把麻雀打下来。万里无云的日子里,他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握拳,自然下垂,挺胸昂首,结果五秒钟后,坠下的不是麻雀,而是麻雀拉出来的一团屎。“那团夹杂着白、黄、绿三种颜色的鸟屎,精准地命中了匹超圆睁的右眼——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大、最美的一团鸟屎。”在班级一直被匹超压过一头的少年,那天心里不知有多解气、多快意。
吴昕孺在写作中尽力还原本真自我。《罗岭少年故事》以作者少年时光为底本,当初不经意的糗事,有意求取却往往陷入尴尬的丑事,皆有令人啼笑皆非却童趣十足的流淌。在他笔下,童心的荡漾是最高境界的真实。真实的童年不正是这样的吗?哪来负担或压力?遇到悲伤、痛苦之事,也很快被即将到来的某一种快乐迅速稀释、淡化至于空无。
其次,作者想象力丰富。以少年视角看待万物,无不亦真亦幻,充满好奇与神秘。来历不明的肖老师,主动为即将不久于人世的宋大伯治病,征得其家人同意后,只见肖老师随后于窗台上捉了一只蚂蚁,从裤兜里拿出手电筒照着,几秒钟后,他让宋大伯张开嘴,将那只蚂蚁放进去。“他继续捉蚂蚁,一只一只捉,用手电筒照一照,再送到宋大伯口里。送了几十百把只之后,肖老师不再捉蚂蚁,而是用手电筒直接照蚂蚁,凡是找到的蚂蚁自动往床上,往宋大伯身上爬,一直爬进他张开的口里。不多时,爬往宋大伯口里的蚂蚁排成了长长的队伍,络绎不绝。”药引子是蚂蚁,治病辅助工具是手电筒,就此两样,经过一番折腾之后,宋大伯后来竟得以痊愈。蚂蚁固然是《蚁灾》中的主角,不也是少年某段岁月的主角?万物皆备于我,如此看来,少年的罗岭村哪里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可以穷尽的?
还有那只独眼狗,与渐渐爱上晨跑的少年如挚友般相处几天之后,无端地消失了。也许是少年想要前往它住的地方,令它害怕或者不习惯?难道在外头与少年一段时间的跑步或玩耍,即是它传递善良与爱意的极致?总之,它再没出现过。可是,在少年心中,它又好像从没离开。“从中学、大学,一直到现在,无论辗转到哪个城市或乡间,我都会准时起床,出门跑步。每次晨跑,我的脚边都会有另一个影子,它始终保持着与我平行,不领先半脚,也不落后一腿,无论我将终点定在哪里,它都能保证和我同时到达。”每次跑步,都有它陪着。不仅仅这样,“这么多年来,我经受了无数的挫败,陷入过深重的迷茫,每当我要放弃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它,它的瞎,它的瘸,它戏剧性的出现与决然的离开,它不同于任何其他生命的自成一格。”这就是人与动物默契、交心之后的神奇之处,它可以成为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不可替代的伙伴,甚至它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罗岭少年故事》飘散出各种动物的气味,是那么普通而日常,有着典型的中国南方乡村的风味。在很多人特别是当下很多少年看来,它们是臭的、脏的、但它们却成了帮助罗岭少年成长的不可或缺的存在。于是,这本书给我们带来反思:时下我们的孩子大部分时间都在教室和作业中度过,是否也要想办法让他们走进五彩缤纷的大自然中,让他们与各种动植物交朋友,这样才会有真正健康的体魄和健壮的精神?
《罗岭少年故事》无疑是一部以人与动物交集为线索的成长记。当我们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丛林里感到茫然失措,无所适从,乡村的一切或许正是我们苦苦寻觅、可以皈依的心灵故乡。
责编:刘畅畅
一审:刘畅畅
二审:印奕帆
三审:谭登
来源:华声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