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残雪。图/陈小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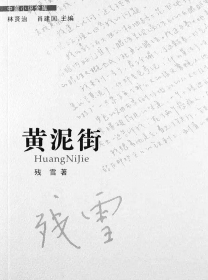
今年十一黄金周的朋友圈和往年有点不同。刷屏的不再是热门景点和美食打卡,而是一次次与文学有关的追问和普及。
残雪,这个带着圣洁与肮脏两极意义,又充分统一的名字,第一次以无与伦比的力度与频率进入大众的视野。
短短一周时间,作家残雪,这个现年66岁、出道30多年,写了700多万字,被美国和日本文学界誉为“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学最具创造性的作家之一”的长沙人,第一次在国内完成了从“小众”到“网红”的转身。
当地时间10月10日,瑞典文学院揭晓2018年和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两个奖项,结果表明残雪再一次与诺奖擦肩而过。
外界评论依旧汹涌。拥护者表示“残雪并不需要诺奖做加冕的王冠,她的艺术独特性及价值,与能否获奖无关”。质疑者则再次批评残雪“作品乖戾、压抑、费解到令人难以接受”的写作风格。
其实,无论诺贝尔文学奖开奖结果怎样,残雪都是胜者。作为“文学湘军”的一员,残雪借此进入公众视野,让近几年备受冷落的文学,吸引了大众的目光,也给了中国文学一个思考的契机,为何进入世界文学历史的作品却不被中国人所熟知?我们的《重读文学湘军》系列报道也从此开篇。撰文/潇湘晨报记者储文静
是谁在看残雪作品?
在湖南省博物馆工作的陈华丽最近几乎每天都会刷一刷跟残雪有关的信息。作为一名残雪迷,她甚至曾经觉得长沙对于她的意义,可能就是偶尔能够在烈士公园或者别的地方与残雪擦肩而过。直到后来她才知道残雪虽然是长沙人,但似乎是在北京密云定居,近两年又搬去了西双版纳,并没有住在长沙。陈华丽也一直没有机会与她擦肩而过。
陈华丽十几岁时就开始在文学杂志上看残雪的小说,因为年纪太小的缘故,很难看懂。大学时在一本小说合辑里看到《苍老的浮云》,仿佛开悟般的,被那些文字强烈吸引了。因为时间久远,书里很多情节如今已经记得并不真切,但她印象里还一直有一个瘦削苍白的中年女人,在午后老鼠一样咯吱咯吱啃酸黄瓜,屋外的玉兰花啪嗒啪嗒地掉下来,像一朵朵用过的卫生纸。当时看的时候,脑海里满是酸黄瓜,她牙齿都酸了。多少年过去,这个牙帮子酸疼的感觉,一直还在她的脑海里烙印着。
“我看那本书的时候差不多20岁,整个情景让我看的时候就比较代入,觉得那个人就是我。”陈华丽说,
“主要是那种意境,她不是一个设置故事情节的高手,但是她是设置意境的高手,看了她的书我会陷入那个情绪出不去。可能是觉得那种夏日有雨睡醒的午后,不是岁月静好,不是暂时的百无聊赖,就是生命本身非常没有意义。荒诞无趣的此在。”
“读不懂”,是很多读者对于残雪小说的一大感受,也因此有很多人不喜欢她的作品,觉得她表现手法太西方了。大概也是因为运用了较多的西方文学因素,残雪的作品在国外受欢迎。但陈华丽觉得“写作技法应该是共通的,她写的内容,以及人物的行为方式,还是很中国的”。
与陈华丽一样,北京大学博士毕业生赵燕灵看的第一本残雪作品,也是《苍老的浮云》。那时赵燕灵还在读高中,看的是长江文艺出版社的一套文学丛书,有结构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荒诞派小说等。残雪的《苍老的浮云》是其中一本。对于这个作品,赵燕灵的第一感觉是“生理不适”,常常看到想要呕吐,可想而知,残雪的作品有多么强大的冲击力。
“但奇怪的是,她的文字竟然能入梦。梦醒之后,提笔记下来的小说,居然和残雪的作品有点像。”赵燕灵说,总之,当时通过那套丛书记住了残雪的名字,她和马原、张辛欣、张抗抗、王蒙、余华、孙甘露或者扎西达娃都不一样,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如今回过头去重看她的小说,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难以言传,但现在可以归结为美。恣意生长,奇诡变幻,讽喻兼而有之。”
赵燕灵觉得残雪有一种令人过目不忘的美,当把书本合上之后,更能体会她的悲悯与温柔。以赵燕灵的经验,残雪的短篇和长篇的精神内核是一样的,看懂一篇就能理解她。她建议大家读《梨园纪事》,读十遍,也许就理解残雪了。
媒体工作人宇人是先喜欢残雪的哥哥、中国著名哲学家邓晓芒,然后才对残雪的作品产生兴趣,继而喜欢上残雪的。宇人觉得,“残雪的小说里有纯粹的生命之力,从哲学上读懂了很有力量。她不仅写小说,也写哲学著作,她是古典中的现代派,现代中的古典派。”
并不令人意外的是,随访的三位读者中,陈华丽、赵燕灵、宇人都是名校历史系的高材生,爱好哲学,硕士以上学历。也许,这是一个巧合。也许,这便是残雪受众圈。
“残雪的作品文本本身进入有一点难度,可能就会拒绝一部分不喜欢思考的读者。有一定哲学基础的读者,进入残雪的作品可能稍微容易一点。”残雪作品的责任编辑、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陈小真如是说。
陈小真在读大学时就读过残雪的《山上的小屋》《黄泥街》等中篇小说,以及她的许多访谈和谈论中国文坛的文章。后来陈小真来到湖南文艺出版社,陆续编发了她的几篇小说,再后来签下了她所有作品的数字版权。如今,市面上几乎所有的残雪作品都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大多经过了陈小真的编辑。
陈小真与残雪交往的头几年大多是通过邮件和电话。第一次见面是在2014年10月,现在残雪谢绝各种社交活动,潜心写作,但依然与陈小真保持着频繁的邮件联系。陈小真说,为了读懂残雪,他看过一两百本哲学原典。有了这样一个基础,进入残雪作品能稍微容易一些,但即使这样,他依旧不敢说所有的作品都看懂了。
“残雪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她需要有更多的读者。”陈小真说。
残雪:“我非常希望更多人关注高层次文学”
诺贝尔奖热门人选爆出时,许多包括中文系学生、媒体从业者、文艺工作者在内的文学爱好人士都发出疑问“残雪是谁”,更不必说普通大众。
从1985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至今她已出版超过60部作品,但从未获得过国内任何权威的文学奖项,也并未进入大众的视野。
可以算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吧。四年前,残雪获得国外多项文学奖提名,并斩获美国第八届最佳翻译图书奖,成为获得这一奖项唯一的中国作家。欧美、日本知名评论家对她的作品不吝赞美之词。日本还成立了残雪研究会,创办了《残雪研究》杂志。在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的书店里,中国文学栏目下,残雪的作品总摆放在醒目位置。
其实,早在1987年,残雪的多篇小说就登载在美国文学期刊《形态》上,残雪从事写作三十年,几乎每年都有作品在国外出版,她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主要有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瑞典语、意大利语、越南语。迄今为止,共有近三十个外文版单行本,是作品被翻译出版最多的中国女作家。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国际影响力的原因,还有其他很多因素。翻译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把国内的作品介绍到国外是需要精湛的翻译的,而翻译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作品的质量。残雪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语言平和,富有诗意,易于翻译。
国内被称为小众,国外大受追捧,面对这种情况,残雪本人倒是很淡然。她从不否认她的作品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她表示:“我生活在一个追求理想的家庭氛围里,而且接受了西方的理想主义,才能一直保持创作力。如果不学习西方文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在众多的西方现代派作家中,最常被人们拿来与残雪进行比较的是卡夫卡,两者不约而同地以一种荒诞的呈现手法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展现与反思,构成了中外文学史上一次扣人心弦的心灵互动。残雪却并不认可这样的说法,“我们完全不同,他是受过教育的,有思想结构在其中。我是凭空杜撰,照想象和直觉写作”。她认为,具备了东方文化传统的优势,努力学习西方经典文学,才能对中国新文学进行一次突围,也是对但丁、卡夫卡等人的超越,“我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进行创作,一定能走得更远”。
残雪坦言,她的小说排斥一般读者,“一般人很难进入到里头,那种封闭性令人生畏。从不写这个世界里的事,而是海上冰山下面的部分,属于人的原始欲望。”
“我的作品是那种寓言式的作品,扎根在现实中间,指向未来的理想主义。不管是精神世界还是日常生活,看我这种小说都会得到很明显的改善。”残雪说,“正是因为近年来,国际上我这个门类的优秀文学作品不多,才受到西方学者和出版社的重视。他们同样承认我的写作是高难度的。但是读者还没有起来,这些广泛的影响还不够。”
残雪说:“我的读者是那种热爱生活,有理想追求的、读过很多文学作品和一些哲学作品的、高层次的读者。”
在中国文坛,残雪像一个“异类”,她刻意与文学界、与其他作家保持距离。现在定居在西双版纳的残雪每天都在写作,规定每天写一个小时,不需要灵感。“没有构思,也没有提纲,积累久一点,可写长一点。有时只有小的意象,就写短的。”残雪描述这是一种“自动写作”过程,她认为自己是完全跟着笔走的作家,“用心,而不是用脑去写作”。
诺贝尔奖赔率榜单被爆出之后,残雪每天都会接到无数媒体记者的访问,但她不以为意。奖项揭晓后,她也并不失落。她一直表示,这个奖目前的希望并不大。等到多少年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高层次的写作者、研究者越来越多,读者自然也会越多。读者的接受度积累起来之后,可能会有得到诺贝尔奖这个希望。
即使如此,能够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残雪还是非常欣慰和开心。她表示这首先是一种进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很多,包括政治、地缘、文学等多重因素,这一次她能进入预测“热门榜”,说明诺奖正在更加重视文学特别是高层次文学的价值。对此,残雪表示:“我从事的是高层次的文学创作,读者是很小的一个群体,但是我非常希望更多人关注高层次文学。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能让我的作品更快、更广泛地走进读者,当然是很让我开心的一件事。”
聂茂:残雪作品中的人民性,是文学湘军的一种精神
“在残雪的作品中,生存的迷茫、现实的伤痛、精神的恐慌都是底层人物的真实写照。小说中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展现出惊人的愈合力量,是因为作家赋予了它强大的精神功能。”当代作家、评论家、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聂茂教授这样评论残雪。
残雪在作品里书写了大量的底层人。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自己就是底层人,在底层干了些年头。我理解的底层就是日常生活,我是非常热爱日常生活的。”残雪的人生经历颇带传奇色彩:她出身官宦和书香门第,父母兄弟身世浮沉,尝尽世态炎凉。残雪本人当过待业青年、医疗站学徒、机械厂工人、个体裁缝,最终成为专业作家。
“说到底,残雪跟许多文学湘军一样,把笔触指向底层。指向底层就是文学湘军人民性的重要表现之一。”聂茂说。
聂茂在他的新书——“中国经验与文学湘军发展研究”书系(共7部)的第一部《人民文学:道路选择与价值承载》花重要笔墨研究了残雪和她的文学作品。书中梳理了关于残雪文学作品评论的三个时间分段:20世纪80年代的争论质疑期、20世纪90年代的阐释分析期以及新世纪的宽容期。
聂茂说,20世纪80年代文学方兴未艾,各种学说涌入中国,残雪作品虽说从属于先锋派,打着割裂现实的旗号,但其颇为极端的风格还是难以受到保守国人的认可。1985年残雪在《新创作》的第一期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污水上的肥皂泡》,将一种“异类化”的文学创作形式带入大众视角,其称为“新实验”文体。1986年,在发表《黄泥街》、《苍老的浮云》等作品后,残雪在国内引起了更大的争论,1987年,残雪作品被卷进了国内“真伪现代派”的讨论当中,既作为创新失败的典型予以批评,又受到国内外某些媒体、评论家的肯定。此时,相较国内外而言,对残雪的评论在国内更多的是质疑和否定,而国外则是一种欣赏和包容的态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人心态日渐开放,不再纠缠于残雪作品好不好看,看不看得懂,文学界对残雪的解读趋向多元化,一般而言,集中研究残雪作品的梦魇意象、诗意内涵、文本形式和域外文学比较研究等几个方面。在某些著名教材如洪子诚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就对残雪存而不论。而立足于创新意义的教材对残雪则给以较高评价,如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施可训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田中阳、赵树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等。
进入21世纪后,残雪的小说逐渐为大众接受,对残雪的研究也出现了深度和总体上的突破。许多研究者不再把残雪视为一个文学个案,而是将她纳入更为宏阔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中,残雪与西方文学传统在精神上的关联与默契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
残雪的作品有着很大的争议,她的小说之费解已经达到了令习惯于在前因后果的文学叙事和意图明朗的故事情节中找寻意义的读者难以接受的程度。怪异的表现手法,夸张、荒诞的人物性格,梦魇般的气氛,故事内部时间的断裂、空间的交错等,都为残雪的小说打上了鲜明的无法与他人作品混淆的印记,也给读者和研究者造成了审美上的巨大冲击。
聂茂认为,要更好地理解残雪文学创作的源泉以及其具体文本中出现的令一般人匪夷所思的场景与意向,就必须对其家庭与成长环境进行溯源。1953年出生在长沙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庭文化氛围浓厚,用她自己的话形容,“父母都是那个年代的所谓理想主义者”。1957年父母被划为右派,父亲被关“牛棚”,母亲被下放劳改。幼时的她遂跟随外婆生活。小学时接触文学,小学毕业后适逢文革而主动辍学。童年的家庭亲子关系和天生的个性,使得残雪自童年起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一种孤独敏感的特立独行的文学气质。故乡,是残雪作品中绕不开的主题。于他们而言,故乡从来不是思念中的乌托邦和精神的避难所,而是社会中的鲜活人物和自然界的绿色枝叶、繁盛果实。
“文学湘军从不以凌驾生活的姿态书写当下,也不以漠视理想的态度表现苦难,像残雪这样,一直面向时代、面向脚下的这片土地,尤其是故乡,无论是物质意义上还是精神层面上,都是沉甸甸的。”聂茂说。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储文静
责编:印奕帆
来源:潇湘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