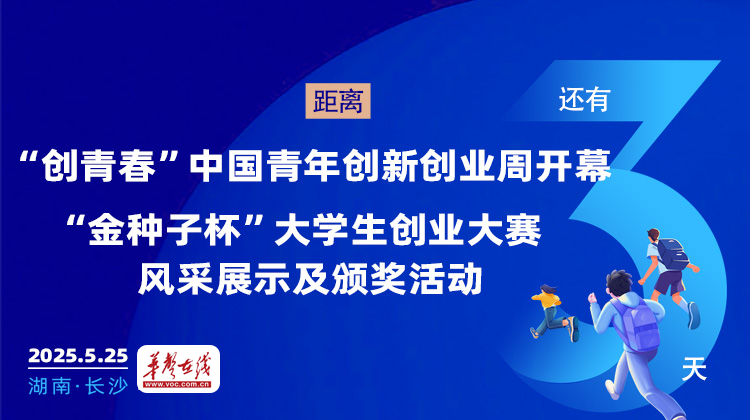邓朝晖
茶马古道也看到过几个,在安化、汉寿都有。听说安化的茶马古道留下的遗迹更多,青石板上有马蹄踩过的印。所以我总以为,茶马古道就是山里的一条路,沿途有换马的地方,就成了驿站。驿站人流量大,时间长了就发展成一个集市,商贾云集,客栈酒肆等等都有了。
然而这次去的一个茶马古道,竟是以水运闻名的。
临湘聂市镇,离岳阳临湘市不远,十几公里的路程。刚下车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只觉得是一条老街,但保存得并不好,石板路大多经过修缮,所剩青砖不多。街边的房屋也新旧不一,各种年代的都有。
听当地人介绍,才知道这里过去以茶著称,是我国唐宋以来茶马古道和清中期以来中俄万里茶路的南方起点。清康熙年间至整个民国年间,晋商在此办厂,制作砖茶销往我国西北边区和蒙古、俄罗斯,乃至欧洲多国。比安化的制茶时间早了30多年。
聂市茶由码头下到聂市河,经黄盖湖入长江,经汉水至樊城老河口上岸,遂改用大车陆运,穿河南至山西大同,然后分东西两路分销。东路,至外蒙古、俄罗斯,少数至我国黑龙江的漠河、海拉尔等地;西路,延伸至新疆的乌鲁木齐、伊犁、塔城各处。
聂市镇老街有方志盛、牌楼口、万寿宫等十一条小巷通往聂市河边的大码头(据说也有十一个)。我下到其中一个码头,台阶是青石板的,台阶和旁边的墙上都滋生出很多野草藤蔓,聂市河水不宽但清澈,河岸有绿得发亮的水草,还有一畦畦居民们开垦出来的菜地,几个人戴着草帽,正躬身在菜地里。
朋友们在另一个码头看到了绣楼,说很窄的一个阁楼,仅容得下一个人。这印证了聂市当年的繁华,清代、民国期间,它被称为“小汉口”,码头一带的房产只有富商巨贾才置得起。我想象那个绣楼上的小姐,虽然被拘泥在几尺见方的小楼里,但她的面前是一个多么开阔的世界啊。
我曾经在几篇文章里提到,以“市”为名的地名在以前一定是个繁华之地,澧水边的津市、沅水边的陬市,而且就这几个地方看来,似乎可以得出,以“市”为名的地名当年的繁华也是因水而起,因水路运输带来物资的丰沛、人口的密集、文化的兴起。所以,虽然如今聂市老街有些尴尬,既没有保存得像洪江古城、里耶古镇那么完整,又没有像很多新兴城镇一样改头换面,我还是有些喜欢,为那些斑驳的马头墙,为那门楣上的石雕,为许多无法复制的精致与破败。
即使哪一天老屋、青石板、码头、绣楼全部消失了,那河水还在,聂市河仍然会归入黄盖湖的怀抱,带着三国时代的英雄气魄,浩浩荡荡直泻长江。
在东、西、南三个洞庭湖中,南洞庭是知道得最少的,比如它流经的地方,益阳南县、沅江,都只是路过。南县的茅草街,因处在湘、资、沅、澧、赤磊洪道、藕池西支、沱江七大水系交汇处而著称。这个地方我至今都记得,童年时代母亲带我出门,要在这里过渡。我们的车在岸边等啊,等渡车的船开过来,一趟一趟的,总也轮不到我们。那时候南方的人出门,除了坐车,还得过一条又一条的河流,所以童年时代的远行总带有一点悲壮的色彩,它让我知道出门有多难,而且那种等船的无奈,在河上,特别是在洞庭湖上飘泊的感觉,让幼年的我对生命产生了敬畏。它让我知道,茫茫无边的湖水有多强大,而我们如同草芥。
从临湘回益阳的路上,车子在省道上疾驰,走了一段,左右两边各出现一条河流,朋友说,湘江快要跟资水汇合了。果然,很快,我的左手边出现了一个湾,像两只手臂抱在一起,“就是这里!这个地方叫临资口。”真好,又有两条河流握手言欢。
这些日子以来,我不断地看到河流们握手言欢,沅江入洞庭,沧浪合流,汨罗江入洞庭,聂市河入黄盖湖,湘江资水交汇,长江、荆江、洞庭三江交汇……有时候,他们像一个个平躺着的人,有人的喜怒哀乐,也需要亲人、家族、朋友、子嗣……
只不过,他们比人多了份长久、缓慢与从容。
责编:欧小雷
来源:华声在线